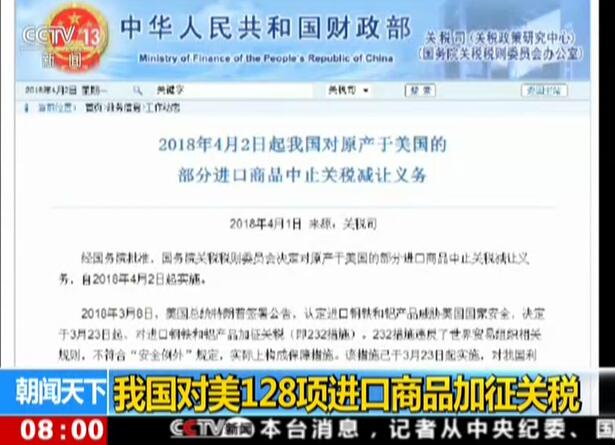中国古典美学关于灵感的命题是和魏晋玄学相联系的,既然艺术是天才的表现,就不能否认其灵感一词的说法。
按照庄子精神解释创作过程,“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去形忘智、沉思冥想的精神状态是从自然之“道”获取“灵感”的最好途径。而陆机的理论,则与儒家仁爱观相联系,认为诗是充满和谐色彩的图画、令人神往的音乐一样,诗人是感兴方浓时进行创作的语言巨匠,是宇宙先知。唐代诗人司空图在他的《诗品》中,以带有道家神秘主义的观点解释诗艺与创作,认为是那自天而降的灵感,通过二十四层的品级阶梯,最后引导诗人进入迷离恍惚的境地。灵感于是通过四周自然界的作用,磁力般附于诗人,诗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自然界的美唤醒诗人的灵感,并将它引向“太阳”之境,去领悟“伟大的和谐”之道。
灵感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活动,它长期潜伏于艺术家潜意识之中。在某种机缘下,“灵感”成为创造性高潮到来的信号,成为精神高度集中自由关照的闪光。这是一种直觉式的顿悟,是一种突然发现的心灵奇迹。我们承认“灵感”的存在,不等于把“灵感”绝对化,以至否认理性活动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反,灵感恰恰是感性经验长期积累,理性思索持续进行的结果。或者说,“直觉”和“灵感”,是感性经验向着理性洞见飞跃的醒悟点。王国维谈到词的第三种境界时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用来描述“灵感”来临前的心理寻觅过程和“灵感”到来时的审美惊喜,似乎是恰当的。
艺术创作中“灵感”一直潜伏或突破出现,画家苏里科夫在冬天一片雪地上,看见一只低垂着翅膀的乌鸦,突然获得女圣徒莫洛卓娃形象的契机。用黑格尔的话说:“它不是别的,就是完全沉浸在主题里,不到把它表现为完满的艺术形象时决不肯罢休的那种情况。”
石鲁创作的名作《宝塔葵花》,他对宝塔的感情可以说蓄池、积淀了二十多年的!早在1940年他满脚血泡地来到延安时,作为喜好画画的他,此时非常激动。1948年、1949年延安光复和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回到延安,每次都很激动。后来即1956年冬天,他曾画过一幅写生性的《延安宝塔》,是如实性的描写,他一直想找一个合适角度表现这种追求革命的感情体验。直到1961年秋,他又去延安,在飞机场偶然回头一瞥,透过一排排向日葵,看到了宝塔,这时他对宝塔蓄池、积淀了二十多年的感情找到了表现的语言,回到西安后很快创作了《宝塔葵花》,这是他“回头一瞥”给予的创作激情。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的表现方式是将画家本人主观感情对生活客观的溶解与再造,这就需要画家本人对于生活的认识表现于画面,在这冗长的过程中无时不体现出画家本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表现及对画面认识的内涵,这也要画家本人长期的观察、体验、摄取、积累,找到生活中与画家本人心灵共鸣的落脚点,捕捉时代的精神之美,在忠于生活中不断地去表现自然!
当然,艺术创作在不同艺术家那里千差万别,偶发性的“灵感思维”比起恒常性的理论思维似乎更难找到一定之规,似乎有它的神秘性。所谓神秘,并不是说它不可知,而是我们认识力的局限,使我们对“灵感”现象还不能透彻了解,还不能解释清楚,不能曲尽其妙。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灵感的奥秘,不仅是它何时到来,何时闪光,难以预测,而且,灵感将以“顿悟”还是“渐悟”方式出现,更难以把握。莫扎特能够在一个晚上写出一首《唐·吉奥凡尼序曲》,而思路比较缓慢同时比较深刻的贝多芬,在一部交响乐曲上花了十年功夫。前者在灯火明灭间显示了超凡出众的才华,后者十年磨一剑,又何尝不是以他巨大的智慧和天才证实了人类可能做出怎样不可思议的奇迹!
艺术的直觉和理性,感觉和联想,不仅关系着一幅作品的创造,有可能启发了一个流派,一个新的审美领域的开拓。抽象画在我们处于封闭状态时,何等生疏、荒谬,但是,当我们处于开放条件下,从人类审美实践上、美学理论上,从技术美学、建筑美学、绘画美学不同角度效应上,来认识抽象艺术时,就会承认,抽象画不仅有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而且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一定的贡献。抽象主义的发端,从它的创始人康定斯基个人心理反射来研究,“灵感”思维甚至以错觉、误解的方式在闪光。从画家感悟的偶然性、触发点来看,拿它和我国诗论的名句做一比较“作诗火急追亡逋,情景一失后难摹”,似乎有着贴近、暗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