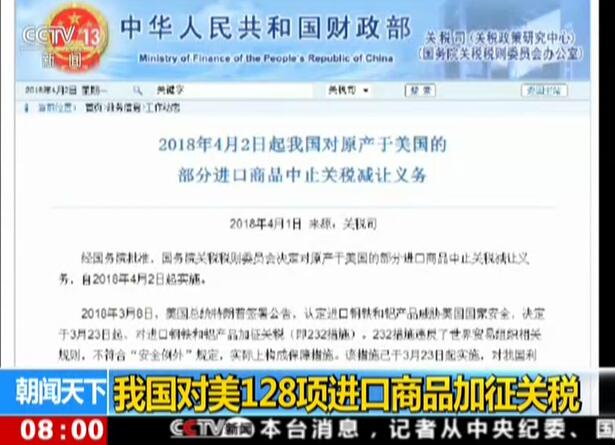普惠金融发展要“道”“术”结合
对话经济学家杜晓山
不管是全球,抑或是我国的普惠金融,都是沿着小额信贷—微型金融—普惠金融的历程逐步走过的,也都是从具体实践到理论提升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特别是近十年来,包容性金融,或是现如今已被定义的“普惠金融”,对农村金融的服务覆盖、质量提升都起到了极大作用,社会特别是金融业内也逐步认可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可参与主体的作用方式以及数字普惠的推动作用。
本周,《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我国“小额信贷之父”——杜晓山。他以多年来的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实践,讲述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了我国未来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
实践到理论的深化
《金融时报》记者:普惠金融的理念在我国是怎样产生的?又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杜晓山:无论国际或国内,普惠金融都是从实践到理论深化的过程。最初,被更广泛使用的是微型金融。在弱势群体得到微型金融资助,经济实力增强后,他们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在增强。世界银行对微型金融的基本定义就不再够用了,这个概念随之被突破,“普惠金融”形成。这本身既是个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界定过程。
从我的个人判断来看,国内普惠金融发展到目前,可以被分作4个阶段。
最初是从1993年至1996年,主要是国际援助力量、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系统试图解决农户特别是农村地区中低收入农户的贷款问题,这也算是中国小额信贷,或者更大范围普惠金融的起步阶段。
1997年到2000年是第二阶段。我国在1994年提出并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7年,国家层面正式接纳了小额信贷(或微型金融)的理念,意图借鉴国际经验开展扶贫贷款试验,政府大规模地在全国贫困地区以政府贴息、担保和农行本金进行对贫困农户的小额扶贫贷款。2000年,我国也宣布了八七扶贫攻坚的目标基本实现。
2001年至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是第三个阶段。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形成坏账率很高,也就是说,从金融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没有找到适合的发展模式。但微型金融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被广泛接受了。2000年后,对农户进行信用评级并发放对应额度贷款以及格莱珉银行的联保模式被广泛实践, 2008年,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试点3年后,共同推出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
2006年至今是第四阶段。2006年,人民银行课题组和小额信贷联盟联合翻译了联合国2006年“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其正式接纳,并在随后得到快速发展。
一系列的实践证明,普惠金融不是福利性的,也不是纯商业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其重点是服务弱势群体。
保本微利保障普惠可持续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理解普惠金融的非福利性和非纯商业性?
杜晓山:非福利性和非纯商业性意味着,普惠金融要保本微利并可持续发展,国际上的成功实践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
普惠金融是在没有过多外部补贴情况下的保本微利、可持续。目前,我国很多商业性金融机构在财政贴息、担保和备付金的“督促”下开展的是“特惠金融”。因为其无法带来最大利润以及较高风险的特征而要求特惠政策,这种思想是存在问题的。商业机构在获得高资本回报率的同时,也应兼顾一定的社会效益。我国也试图发展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以增加农村金融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金融的供给不足,但普惠金融中低端需求的满足仍然依赖于过度的财政贴息和风险分担。
成功服务中低端客户的格莱珉银行的起步是很有利的。除了国际援助的赠款和低息贷款,他也获得了本国政府的巨大支持——免税,持续以政府资金入股,这也为其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和社会资本。
我国不应只被动等待商业性机构转变思路,自觉自愿开展普惠金融,可以考虑设立或鼓励设立拥有公益性的价值理念,同时遵循保本微利可持续的经营原则的小额信贷机构,并给予精准有效的、非直接补贴的政策倾斜。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有些很基本的问题上是有问题的。而金融监管当局更应站在全社会来考虑问题,发挥评价、考核等指挥棒作用,以引导各类机构主动充分践行普惠金融。
考核应注重综合性和长期性
《金融时报》记者:指挥棒作用的发挥需要注意什么?
杜晓山:这首先涉及对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构建。目前的体系构建在国际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一定会有不完善的地方,我国在借鉴国际体系时也应考虑本国发展特点。据我所知,部分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已尝试设计适用于本地区的考核指标体系。无论是从地区纬度,抑或是机构纬度进行考核,都应综合金融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等多个一类指标。
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发挥指挥棒职能,其实也是对机构价值观的塑造,考核的指标体系也要兼顾好业务绩效和社会绩效。而对于社会绩效的考核,在我国一直是被忽视的部分。同时,在考核指标体系完善搭建后,还要有及时的监督跟踪和评估,并应设置具备权威性的奖惩制度,以促进考核真正有效落地。
另外,就是银监会和人民银行都在强调的,尽职免责制要落实。对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和“三农”业务的专项考核,应对其商业可持续性和不良率予以适度让步,更多地考核客户群体的多样化、覆盖率以及服务质量等指标。如果仍要求从业人员无意义地对普惠金融范畴内的不良负担终身责任,具体实施是很难开展下去的。
勿让“木桶效应”制约数字普惠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依靠数字普惠发展普惠金融的说法?
杜晓山:对于数字普惠,我认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解释。
数字普惠在效率、成本和准确率等方面确实给予了金融很大的方便。但其短板也不可忽视——我们在使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时仍不完善;数据的有效性无法保障;我国的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地区,数字金融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不到位,数字鸿沟严重。
数字普惠推广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据部分学者抽样调查,我国贫困地区智能手机的覆盖率只达到20%,其中真正使用智能支付和智能金融的就更少了。我国的移动支付技术、人均服务网点数等方面是处于世界中上水平,甚至领先水平;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防止数字鸿沟,逐步填补(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我希望也主张,数字普惠能够在更广范围内发挥更大的效能,但前提是,社会整体在取得成绩时也不忘弥补短板。
要有情怀 也要有方法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未来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杜晓山:我从事小额信贷也有很长时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户需要的是真心实意而踏实的帮助:需要站在客户而不是机构或个人的角度考虑;同时,也需要不断的提升业务能力。即使是现在有了更多工具和技术的支持,普惠金融仍不可以被单纯地化繁为简。必要的内控和风控手段不可或缺,要有完整的监督机制。
农村信用环境总被认为是不好的。除了产业、政策等无法控制的因素外,资金安全性仍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机构手中。在贷款未被偿还时,如果不及时追债、查明原因,就可能造成羊群效应,进而形成地区的系统性问题。包商银行采用的、可以用于小微企业贷款的IPC微贷技术则更为复杂,需要综合考察企业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通过对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制作,详尽了解企业盈利和资金流动状况,以更为完善的场景搭建保障贷出资金的安全性。因此,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中不应以制度和程序的简化为唯一目的,而是差异化和低风险服务弱势群体的关键。
相对于城镇的普惠金融,在农村做普惠金融需要更大的情怀,各参与主体要以情怀和正确的价值观,调整业务操作兼顾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
我经常说,这个情怀或价值观的问题是“道”,而所使用的技巧和风控手段是“术”。金融机构考虑如何解决抵押担保难题、如何提升社会整体信用水平,这都没错,这是术的问题;但同时,政府更需要出台政策,启发有“道”的人或机构更积极地参与到普惠金融的推动工作中来。